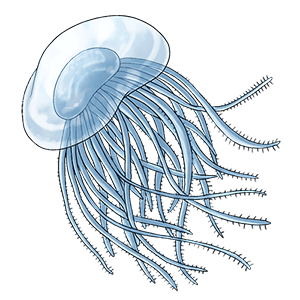本帖最后由 狼狗杰 于 2016-8-23 00:15 编辑
回复 30# 狼狗杰
第二十七章(2016/8/2)
「公爵夫人,」绿衣的狼人骑士洛奇从巴鲁斯身边起身,在安哈特伯爵所居住的客房门口迎接被巴鲁莎搂著的佳楚德。「怎么回事,巴鲁莎?」洛奇看著佳楚德脸色苍白,忍不住摆头询问他自己的妻子,「公爵夫人是不是受伤了?」
「她刚才被公爵掐脖子,」巴鲁莎回答道。「巴鲁莎!」佳楚德轻声斥责著,「别胡说。」巴鲁莎把她的金眼珠都瞪圆了,「我胡说?」她两隻大手揪住佳楚德的双肩,「他都快把你掐死了,你还替他掩盖什么?」
「本来就该掩盖,」早已经穿上绿色侍从服的黑狼布鲁托走到门口来,「你不掩盖,凯撒的整个家族都会陷入危险。」巴鲁莎听见这话翻起白眼,摆过头去望著黑狼说,「这话听起来像是约翰说的。」黑狼半瞇著眼睛,蓝色的冷光从眼缝缓缓流出,注视著巴鲁莎,一副怒火中烧又隐忍不发的样子。披著熊皮,穿著马裤坐在门边的巴鲁斯站起身来,从旁抱住黑狼,细声安抚著,「我们进去继续收拾吧。我帮你。」可是黑狼挣出了熊皮男人的怀抱,衝著白狼巴鲁莎说,「今夜在公爵夫人的见证下,我就和你把话说清楚。你已经和洛奇结婚。我已经在族人面前宣布脱离伊利诺族,并且不再是提尔与伊莎之子,洛奇的兄弟。」
「布鲁托!」洛奇发出惊叫。黑狼只斜瞄他一眼,又拉回视线瞪视巴鲁莎,「你听到了,管好你的丈夫。别再让他对我说好话,还当我是他兄弟,」他一手紧勾住身边粗壮男人的后颈,让自己的毛脸隔著熊皮紧靠男人的脸部一侧,「我的兄弟现在是巴鲁斯。我不再与你们有任何关係。」
洛奇向黑狼伸手哀声说著,「拜讬,布鲁托,」却被黑狼用另一手拍掉伸来的手掌。「你干什么?」巴鲁莎正要衝上前去,被洛奇抱住阻挡。接著洛奇转过头对黑狼低声请求,「至少祝福我们俩的婚姻吧。」
「我不会祝福一对在週五结婚的笨蛋,」洛奇挖苦道,「而且我希望教会会因为你们在週五结婚而宣布你们的婚姻无效。也不知道这裡的主教是怎么想的,居然会违反禁令让你们在圣子受难的週五结婚。」
「那是我母亲的命令,」佳楚德忍不住说话了,并且摆出高姿态斜视面前比她高大许多的狼人侍从,「你作为安哈特伯爵的侍从,却一点规矩都不懂,不仅批评皇后的命令,还顶撞皇后亲封的两位骑士,应该受到惩戒。」
「请原谅,公爵夫人,」洛奇抓住巴鲁莎双手,却望著佳楚德落下双膝。「你在做什么,洛奇?」巴鲁莎要把双手抽出洛奇的掌握,好扶洛奇起身。但洛奇却紧抓巴鲁莎的双手不放,仰望佳楚德继续说道,「请宽恕我的兄弟,他不是故意要说那些冒犯到皇后的话。」
「别再称我为兄弟!」布鲁托大吼,狼的咆哮声也随著他说话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冒出来,吓坏了房裡还在整理物品的其他侍从与仆役们,「你不是讨厌我对你做的那些事吗?既然如此,就不要再对我好,或者,为我求情。否则,」说著说著,他噘嘴露齿,口水从他嘴角滴落在地,语气变得淫靡下流,「我怕我又克制不住,对你做那些会让我十分快乐的事。」
「布鲁托.提尔森!(Pluto Tyrson!)」洛奇几乎是跳起来地衝到黑狼面前,高喊著他兄弟的名字和父名。巴鲁斯连忙又抱紧黑狼后退一步。不过看来洛奇没有再上前攻击黑狼的打算,他只是瞪著黑狼,瞪到眼珠由纯金变成浊黄,蔓延无数的血丝,「你满脑子就只有那种脏东西吗?我想原谅你。可是你为什么要一直说会让我继续恨你的话?」
「因为我爱你,」布鲁托冒出这句话,抬眼望了望巴鲁斯,后者则撇开视线,望向洛奇裤腿末端露出的脚爪。布鲁托又收回视线望著洛奇,「你如果愿意继续做我的兄弟,就离开巴鲁莎回到我身边,继续与我做快乐的事,我也会离开现在抱著我的这个男人,」他这么说著,还搥了搥巴鲁斯的胸膛。巴鲁斯则鬆开拥抱他的双手,转身背对他抱胸望地。他紧接著说,「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继续碰你的身体,我就不再是你的兄弟,」他伸手从巴鲁斯背后握住巴鲁斯从胸部放下垂在大腿边的右手,「我会是他兄弟。」
「这是我听过最背德的言语,」佳楚德呲嘴咬牙,一双草绿色眼珠流露出极端的厌恶,「跟亲兄弟同睡很快活吗?你这肮脏的狗!」
「不能跟我同睡的男人就不是我兄弟,」黑狼以十分理所当然的语气回应佳楚德的谴责。洛奇气得浑身发抖,身上的毛都竖直了,「你都不愧疚吗,」他质问黑狼,「对我?你对你无数次伤害我从来都不愧疚吗?你觉得你对我做的事是对的?」
「如果你还愿意让我碰你,而且没有约翰来作乱,我是不会介意你娶巴鲁莎的,」布鲁托的言语弄得连背对他的巴鲁斯都转头斜视他:「我喜欢碰你。不管用什么样的手段我都要得到你,就算是约翰所谓的威胁,我也可以做下去。你不是也屈服于我了吗,为了巴鲁莎?你们普通雄性可以为雌性做任何事,我也可以为了得到一个能够伴我一生的雄性做任何事。」
「无耻!」洛奇发出怒吼,握紧拳头举到半空,一副要揍布鲁托的样子。回头斜视布鲁托的巴鲁斯看见这幕也只是转过头去继续看著地面,似乎也觉得布鲁托该挨这拳。但是洛奇终究没揍他的亲兄弟,他甩下拳头,走回巴鲁莎身边,搂住巴鲁莎的腰,「就像你说的,我可以为巴鲁莎做任何事,」他语气恢復冷静,也冷峻而不带任何感情,「我没有像你这样的兄弟。从今以后,你无父,无母,且是无兄弟的人。你不配拥有提尔森这个名字,因为你不是提尔之子。你只是巴鲁莎与我的好友大熊阿布雷希特的侍从。要说我有兄弟的话,」他发出一声冷哼,「他叫约翰,希德勒村的约翰,伊利诺村的约翰,我岳母塔西娜曾是他的保护人。他又称宾根的约翰。而你,」他举起空下来的右手,朝布鲁托伸直食指,「伤不了他。」
「很好,」布鲁托握紧巴鲁斯的右手,把他往房裡拖。房裡的仆役们像没事人那样继续他们手上的工作。布鲁托也抄起刚才他还在床上折疊著的衣服,继续他刚才中断的工作。「我能做什么事?」巴鲁斯把脸凑近布鲁托的脸低声问。布鲁托回答,「帮我摺这些衣服,放进床尾置物箱,等等一起抬上马车。」
「布鲁托!」一直站在房间裡的安哈特伯爵阿布雷希特高声喊道,「过来!」
黑狼叹了一口气,「好好摺,」他吩咐身边披熊皮的男人,「像我刚刚那样举起衣服摊开再对摺,都摺好再一件一件放进箱子,」然后他转身跑向伯爵,「我能为你做什么,爵爷?」他鞠躬说道。「向门外跪下,」伯爵说,「请求公爵夫人和我的两位骑士朋友宽恕你刚才的冒犯。」黑狼很爽快地双膝下跪,并对门外的一对狼人与公爵夫人伸出双手,展示长著黑色肉垫的手心,「原谅我,三位尊贵的阁下,刚才我冒犯了你们。」
「布鲁托,」洛奇又忍不住心软,想走进门扶黑狼起来。黑狼大叫,「别过来!」惊得洛奇停下脚步与动作,向黑狼伸出的双手也停在半空。「别过来,骑士大人,」黑狼的语气恢復从容与恭敬,「我侮辱过你,你不能扶我起来,」接著黑狼把鼻尖指向洛奇身后的红衣贵妇,「公爵夫人,」他喊道,「我愿意为我的无礼接受任何惩戒。」
「不了,」公爵夫人把脸撇向一边对伯爵说,「这狗就交给你自行惩治吧,熊。」
「遵命,」伯爵行了鞠躬礼,再对黑狼粗声粗气地说,「起来。」黑狼依令起身。「回去!」伯爵低声咆哮犹如一头灰熊,「继续收拾我的东西。回安哈特我再整治你。」
「是,」黑狼对伯爵哈腰,退回满布衣物的床边,站在巴鲁斯身旁发愣。「刚才门外发生了什么?」伯爵又扯开嗓子问著房裡的仆役们。「没有,爵爷,」仆役异口同声地回答。巴鲁斯对众多仆人整齐的答话声感到惊讶,环视著答话的仆人们。而黑狼仍然望著床上的衣物发呆。
「抱歉,」巴鲁斯突然说。「什么?」黑狼回神,看见衣服被巴鲁斯捲成一球一球,摇头说,「不,不是这样。我刚才怎么摺的你没看见?」他准备抄起其中一球衣物重新摊开,却被巴鲁斯握住手腕。「这样比较省空间,不是吗?」巴鲁斯反问道。黑狼歪著头细想了一下,似乎觉得巴鲁斯的话很有道理,也开始把伯爵的衣物捲成一球一球。
「我终于知道安哈特很少有谣言流传的原因了,」公爵夫人仍然站在门外,对门内的伯爵说道,「你把下属管教得很好。我相信你也能把那隻狗管得严一点,别让他又到处乱咬人。」伯爵轻笑几声,「喔,公爵夫人。这很简单的。你只要跟仆役们约定好,让他们知道你说这句话意思是要他们回答什么,而又不能做什么,这个约定就会像咒语一样,牢牢绑住他们的心。就算他们有人要破坏这个约定,那也只会有少数最后真的会这么做,」他长呼一口气,「虽然很不愿意想起这点,但这一招确实是那约翰教我的呢。」
「那个巫师约翰?」公爵夫人皱起眉,「说真的,我不喜欢他服侍我的父亲。你讨厌他却又让他服侍我父亲,究竟存的是什么心?」伯爵露出微笑,「喔,公爵夫人,」他回答,「我讨厌他。你讨厌他。凯撒也不是很喜欢他。我为了他让我安哈特的领地有所损失而想杀了他。但我仔细想想,我相信凯撒也明白,这人是个天才,一天能想十个主意,其中有五个烂到爆,另外五个好到不能再好。他是亚瑟王身边的梅林。没有他,凯撒要花费更多代价才能获取金皇冠。」
就在伯爵与公爵夫人透过敞开的门閒聊时,巴鲁斯和布鲁托也一起在伯爵带来的床上把伯爵的衣物捲成一球一球。「是我害了你,」巴鲁斯又说话了。这次布鲁托听懂了,「不是你,」他回答,「是我自己。我把你捡回来。事情发展至今都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在遇到你之前就一直在犯错。」巴鲁斯低声笑出尴尬意味浓厚的细微笑声,听来是不确定该不该笑,「布鲁,」他说,「为什么要做一头坏狼?」
「跟你攻击凯撒后一样,」黑狼把一件衣服擀成圆柱,再把圆柱摺了三摺,「坏事都做了,就没必要再为自己辩解了。」
「如果有人给你臺阶下呢?」
布鲁托噘嘴露齿,无声地笑了起来,「蠢货,」他把巴鲁斯手中的衣物抢过来,「要是洛奇刚才真的说他愿意,我真的会把你一脚踢开喔。」
「我的意思是,」巴鲁斯摇摇头,「你真的认为要继续认他为兄弟,他就必须跟你同寝?」布鲁托本来要开始捲抢过来的衣物,听了这问话停了下来,「哼哼,哼哼哼哼,」从喉咙深处传出嘲讽似的笑声,「他以前一直忍受我,而且又对我很好。我其实知道他不喜欢我这样对他。可是他一直表现出不介意我碰他的样子,又一直喜欢跟我说心事。他一直想假装我没有伤害过他,我是他最信任的兄弟。我就一直欺骗我自己,去想说他也不能没有我,他也需要我的身体,我可以一直重复对他做我想对他做的事。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约翰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话题从洛奇的事突然跳到约翰,巴鲁斯一时无法理解清楚。而布鲁托重复著他的问题,「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杀约翰吗?」巴鲁斯想了几秒才说,「因为他害伯爵的领地被火烧,伯爵想杀他。」
「还有。」
「还有?」巴鲁斯皱紧他的浓眉,又想了想,迟疑地回答,「因为他是一个邪恶的巫师?」
「不,」布鲁托摇头,「他不邪恶。他救了洛奇。他从我这裡拯救了他。他让我没办法再欺骗自己。他让我知道我自己是个坏人。」
巴鲁斯凝望著黑狼的侧脸。而黑狼捏紧手上的黑色裤腿,正要开始捲它,冷不防被巴鲁斯一手揽住左肩,右侧身体猛地靠上巴鲁斯的胸膛。「不管你做了多少坏事,」莽汉抱著黑狼轻声说道,「我都会一直陪在你身边。」
这会公爵夫人还站在门外与门内的伯爵漫谈,「艾丽卡还好吗?」她问起伯爵的母亲。伯爵恭敬地回答,「上帝保佑。她一切安好,身体健康。」
「可惜我婆婆死得早,不然她一定乐意跟你过来。毕竟,我死去的婆婆是她的姐妹,」公爵夫人矫揉造作地感慨一阵,弄得伯爵心裡不禁嘀咕著:你是在我的吴芙希德阿姨死后才嫁给她儿子的,装什么思念逝者的样子?
洛奇和巴鲁莎已经退到公爵夫人身后。巴鲁莎把脸贴到洛奇肩上。而洛奇抽了抽鼻子,似乎闻到了什么,循著那味道把鼻头往下指,看见巴鲁莎右脚用泛黄纱布包扎著的部位正在渗血,惊得伸出双手抓紧了巴鲁莎的两边肩膀,「巴鲁莎,」他说,「你在流血。」
「是吗?」巴鲁莎眼皮下垂,目光涣散,举起一手用食指按上自己的脑侧,「难怪我觉得有点晕。」洛奇赶忙把巴鲁莎搂到门边让她靠墙坐下,并帮她拆开右脚上的纱布。伯爵也赶紧走出房门,同公爵夫人一起蹲下察看纱布下的伤势。「哎,都忘了你脚上还有伤,」伯爵懊恼地叨唸著,「看你在走廊上跑著追人却没阻止你是我的错。」
「追谁?」公爵夫人好奇问道。「追你啊,」伯爵没好气地说。「天啊,」公爵夫人摆回脸来望著白狼,并把左手按上白狼的额,「似乎有点发烧,」她说。洛奇沉默著,端起那隻右脚凑到眼前,注视昨夜小刀刺入造成的深伤。「让我看,」黑狼布鲁托不知何时出现在洛奇身后,他一出声四人都抬头看他,而他身后站著把衣物箱扛在肩上的巴鲁斯。巴鲁斯慢慢把那口重箱子放到地上。洛奇缓缓起身,让布鲁托上前蹲下看著巴鲁莎的伤口。
「伤口是因为刚才跑步才裂开的,止血就没事了。原谅我,爵爷,」黑狼四肢并用爬到伯爵身边,把头钻过伯爵与墙壁之间的缝隙,对房门内喊,「谁有乾净的布?」
「不用麻烦了,」洛奇说,并把右臂上的长袖套从肩上的衣物连结处拆解下来,交给回过头来看他的布鲁托。布鲁托回过身接过绿袖,拿它来绑紧伤口。「喔,原来你还是医生啊?」公爵夫人挖苦著正在替伤口止血的布鲁托。然而洛奇回答,「他本来会是我们族裡的医生的。」公爵夫人一时语塞,只好闭紧嘴巴。布鲁托束紧巴鲁莎伤口上方的踝部,接著舔舐巴鲁莎脚背上的伤口,这是他十年来对巴鲁莎最亲密的动作。如果是今年十月以前布鲁托对她做这样的事,她大概会欣喜若狂。但她现在内心只有感叹:怎么我们三个会变成这样?难道真的像布鲁托说的那样,都是约翰的错?
「恭喜你,骑士大人,」布鲁托突然说,「你怀孕了。」
第二十八章(2016/8/12)
布鲁托宣告伊利诺骑士白狼巴鲁莎怀孕,惊呆客房门外环视巴鲁莎脚伤的三名贵族。「你这个庸医,」佳楚德斥责道,「胡说甚么?你--」「请问公爵夫人有养过狗吗?」布鲁托打断佳楚德的话反问。「当然,」佳楚德说,「我在巴伐利亚有养几隻獾狗(Dackel)。」「你应该知道怎么辨别母狗是否受孕吧?」布鲁托又问。「不知道,」佳楚德答得乾脆。「那请过来看,」布鲁托伸出一隻食指指著巴鲁莎的两腿之间。佳楚德好奇起身,走到布鲁托身边再蹲下。「你看见那地方正在收缩吗?」布鲁托解说道,「那就是受孕的征兆,」然后他抬头,望向身后的灰狼骑士洛奇,巴鲁莎的丈夫。洛奇清清喉咙,「说来十分惭愧,」他边说边用右手食指尖的爪子搔了搔脸上的毛,「我在婚礼前就与巴鲁莎同睡了。」
「哎呀,没什么,」佳楚德脸上展露尚算友善的讪笑,促狭地说,「上帝会原谅你们的,毕竟,你们后来还是结婚了啊。」而黑狼布鲁托仍以意味不明的眼神看著洛奇。洛奇知道布鲁托闻得到,他也知道族人都闻得到巴鲁莎身上有另一个男人的气味,而不少靠近过皇帝的族人肯定知道皇帝就是那股气味的主人。他不知道其他族人是怎么想的。不过他也只在布鲁托眼中两次看见过恶意:一次就是在昨夜的山洞裡,第二次就是现在。
巴鲁莎闭上眼,脸枕在一边肩膀上。「巴鲁莎?巴鲁莎?」佳楚德轻声呼唤,巴鲁莎却没有回应。「看来她是昏过去了,」佳楚德抬头对洛奇说道。洛奇只是耸耸肩。
他其实不在乎巴鲁莎怀的胎会不会都是自己的,就算生下的都是皇帝的孩子他也不在乎。他怕的是他自己跟巴鲁莎会生下像他兄弟布鲁托一样有恶癖的后代,就像他的外公有个同性恋兄弟早逝无后,但外公自己后来结婚也生下了两个同性恋儿子一样。
洛奇和布鲁托的母亲伊莎有三位兄弟,都活得比死在那场野牛围猎中的伊莎还要久,他们分别是萨奇(Saki)、尼奇(Nicki)与艾德蒙(Edmund)。同样都是老洛奇与莉莉(Lili)的儿女,就只有艾德蒙与伊莎有后代,萨奇跟尼奇在伊利诺村裡则是出了名的喜欢男人。洛奇和布鲁托对父母没多少印象,被巴鲁莎的父母芬利斯与塔西娜渐渐养大,才知道他俩的亲生母亲还有这么几位兄弟。艾德蒙舅舅有自己的孩子要照顾,对他姐妹留下来的这两兄弟很冷淡。反而没有孩子的萨奇和尼奇对这两个外甥相当好,常到当时还是酋长的芬利斯那裡来看他们。而且萨奇与尼奇总形影不离。
听说在洛奇与布鲁托两兄弟出生以前,当时还算年轻的娜西塔为萨奇和尼奇举办过结拜仪式。这个仪式被后来到村裡建立教堂的本堂神父宾根的彼得谴责,因而废止。但即使是宾根的彼得,也默认那些之前已经举行结拜仪式的同性伴侣继续像一对夫妻那样生活在一起。只是萨奇与尼奇作为亲兄弟还又透过结拜仪式成为「兄弟」这点让彼得觉得惊世骇俗,所以在每个礼拜日村人们上教堂的时候,萨奇与尼奇只能坐在最后一排,比一般「维持异教习俗的」巫医们离上帝的祭坛更远。照顾洛奇与布鲁托的酋长芬利斯夫妇也有意让小狼兄弟尽量远离这对乱伦的兄弟。
关于洛奇与布鲁托的外公老洛奇有位同性恋兄弟,倒是一向对两位外甥冷淡的艾德蒙舅舅说出来的。那时布鲁托、洛奇和巴鲁莎玩鬼抓人,洛奇刚好撞上他艾德蒙舅舅的小腿。艾德蒙舅舅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生气,而是叹了口气,忽然噘嘴露出顽皮的笑容,把当时才七岁的小狼男洛奇用两隻手从他胁下抓了起来。
黑毛大狼男就这样与三隻小狼人玩了起来,直到他们都玩累了,躺倒在村子外的枯黄草地上。洛奇记得当时他开口问艾德蒙舅舅,「为什么大家都讨厌萨奇舅舅与尼奇舅舅来他们家裡啊?芬利斯不准他们进我们家。你也不准他们进你的家,为什么啊?你们都是我和布鲁托的舅舅啊!」
「因为他们不乾净,」艾德蒙舅舅回答。
「可是我不会讨厌喜欢跟男生干的男生耶,」这时巴鲁莎也插嘴进来。
「芬利斯的女儿。不要说粗话。」成年的黑毛狼男故作正经地对小小的白毛狼女训了这么一句。小白狼把头撇到一边,从鼻孔喷出气来。「我们家族,」艾德蒙舅舅突然说,「已经好几代都出这种不乾净的人了,像我的亚歷斯(Alex)叔叔也是喜欢男人的人,他是我父亲的兄弟,也是你们俩母亲与我们父亲的兄弟。我并没有见过他,但从许多大人口中听说过他的事蹟。他最知名的故事,也是导致他死亡的事件,就是他爱上了一名波希米亚骑士。」
「波希米亚是什么?」巴鲁莎又插嘴问道。艾德蒙又摇摇头,但还是回答了巴鲁莎的问题,「那是一个充满森林的地方,树长得比我们这裡还密,总之,」他继续讲他的故事,「我的亚歷斯叔叔为了这名骑士做出了危害我们族人的事。
「那年你们父母和我都还没出生,我的亚歷斯叔叔在森林裡救回那名迷路的骑士。他把他带回我们住的地方,让他吃喝恢復力气。他还跟那名骑士同睡。据我父亲说,那时亚歷斯叔叔身上都是那名骑士的味道。
「那名骑士恢復力气后便带著亚歷斯叔叔离开了我们,等他们再次回来的时候是隔年春天,还带著一支军队。那时塔西娜的父亲,也就是巴鲁莎的外公,当时的酋长芬里尔带领族人在森林中击败他们,杀光他们,只留下那名骑士与亚歷斯叔叔加以审问。我们从他们口中知道了那名骑士想要我们当时住的土地,所以要亚歷斯叔叔带路,领军来杀光我们,好佔领我们那时居住的土地。亚歷斯叔叔会答应帮助那名骑士,也是因为村裡的男人都因为他喜欢男人而远离他。连我父亲也远离他,儘管他们是同胎生出来的亲兄弟,于是他答应要帮助他所贪恋的骑士去伤害他的族人。不论如何,他伤害了我们,他想帮助敌人毁灭我们,所以我们把他和骑士都杀了,并且和其他被杀死的敌人埋在森林裡,很快就离开那裡,那年亚歷斯叔叔也不过十七岁。十七岁,就能为一个男人背叛我们整个族群,他让我们洛奇家族蒙羞,我的父亲还以为从此没人愿意嫁他。可是你们俩的外婆就出现了,」艾德蒙指著小洛奇和小布鲁托说,「她的名字叫莉莉。要记得她的名字,因为有她,才有你们的母亲、萨奇舅舅、尼奇舅舅和我,也才有你们和你们的表亲,我的孩子们。」
「你认为喜欢跟男人干的男人们都会像那个亚歷斯那么可恶吗?」巴鲁莎问道。「不会,」艾德蒙又摇摇头,「不过我父亲在我结婚的时候跟我说过,他原本担心我成为像亚歷斯叔叔那样的叛徒,因为我跟他一样都是黑毛。」
「嘿,」巴鲁莎用鼻头撞了一下布鲁托,「你也是黑毛,你会成为喜欢干男人的叛徒吗?」
「巴鲁莎,」艾德蒙又纠正道,「不准这样说你的兄弟。」
「所以,」洛奇问大黑狼,「你一直很担心,我们这些小孩裡面,会有人像萨奇与尼奇舅舅,或像你的亚歷斯叔叔那样吗,艾德舅舅(Onkel Ed)?」
「亚歷斯这种人是特例,但在我们洛奇家族裡,喜欢男人的男人,甚至爱上自己兄弟的男人,还有兄弟相恋的状况也不少,这也是我后来自己听长老们说的,我父亲从来没跟我说过这种事情。」
「你能跟我们讲这些故事吗?」洛奇央求道。「我不会讲它们的,」黑毛狼男起身,「我对你们这些小孩讲得太多了,」然后他抛下他们三隻小狼,自己回村裡去了。后来三隻小狼再遇见艾德蒙,他也不再像那次误撞之后陪他们玩,而是保持他长久以来的冷漠,不跟他们说话,他的孩子们遇见他们三个也总是说「我们爸爸不准我们跟你们玩。」唯一的变化是,布鲁托开始跟萨奇与尼奇舅舅常常待在一起,甚至表示想成为巫医,要跟两位舅舅学习。有这个正当理由,芬利斯也同意了,因为除却有乱伦的污点外,萨奇与尼奇的医术其实相当优秀,已经不输长老级的巫医,遑论他们俩的第一位导师,当时才五十多岁的娜西塔。
艾德蒙、萨奇与尼奇舅舅都死在十三年前以搜捕约瑟夫.冯.施莱歇尔为由发生的那场大屠杀中。三位舅舅都英勇战死,其中没有一个通敌背叛村子。
洛奇想起这样的往事,又望了望他的黑狼兄弟布鲁托。他想起他十年来自己一直忍受布鲁托侵犯的理由:他不想製造出一个叛徒。在艾德蒙舅舅说了亚歷斯的故事后,他又向一些喜欢说故事的长老们打听,打听到了他的艾德蒙舅舅没讲清楚的部分:亚歷斯曾强迫老洛奇与他同睡,老洛奇当下反抗了他,之后并疏远了他。洛奇并不愿像自己的外公老洛奇那样,死后有嘲笑他的歌谣流传著:「亚歷斯爱上了洛奇,他的兄弟。洛奇却恨他,不再把他当兄弟,所以他变成伊利诺人的叛徒。上帝惩罚洛奇,生了一对彼此相爱的兄弟。洛奇家的男人之前有这样肮脏的事,以后也一定会有:自己的兄弟是爱男人的,自己生的儿子也会有爱男人的。」
不过,自古流传下来的歌谣不都是这样的故事:你越想避免的事越是容易发生。其实当约翰揭破这一切肮脏的事情,洛奇竟然是鬆了一口气。巴鲁莎既没有觉得他噁心,养大他的芬利斯也没有拒斥他,他至今也没听过有族人议论他身上布鲁托的气味太重,(或许有,只是刚巧都没被他听见而已。)洛奇又往后望,看著站在他身后的巴鲁斯。月光从巴鲁斯背后照过来,把他背光的正面照成一片黑色剪影。洛奇感到恐惧。这个巴鲁斯会是第二个波希米亚骑士吗?布鲁托会变成他们的亚歷斯舅公第二吗?
*
「皇后殿下,」一名老侍女在与一名年轻侍女共同服侍皇后换上睡袍的时候说,「明天是礼拜日,搬迁恐怕不好吧?还要在教堂做礼拜呢。」
「这我明白,」皇后说,「我们只是先准备好,等到了礼拜一就能让家具和行李直接上马车。」
在皇后身处的更衣间外,皇帝已经穿好睡衣,躺在寝宫内的床上。刚才他在花园裡痛斥巴鲁莎行为屡次失当,要巴鲁莎待在苏普林堡等候处分之后,心情便有些不好。他已经都和洛奇夫妇说好这是演戏了,但当他看到巴鲁莎那副委屈的垂耳表情,心都要碎了。然而,为了巴鲁莎和她族人们的安全,还有进军罗马之前的布局,他必须得硬起心肠把戏演下去。
当皇后走出更衣间,寝宫外响起敲门声。「谁?」皇帝出声问道。门外的声音通报,「宾根的约翰,领巴伐利亚公爵亨利希晋见凯撒。」皇帝大喝道,「领他进来!」侍从约翰开了门,扶著跛足的骄傲者进入房内。「天,」皇帝见到他女婿这等惨状,赶紧下床,光脚跑到他女婿面前搀扶著他,「亨利希,我儿,」皇帝特别对他女婿使用「我儿」这个亲昵的称呼,「你这是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白狼攻击我,」亨利希回答。「白狼?」皇帝问道,「哪来的白狼?」
「还能是哪隻白狼呢,陛下?」亨利希高呼,「白狼巴鲁莎攻击我!」
「你在说什么呢,亨利希?」皇帝摇摇头,「那头傻狼怎么可能攻击你呢?」
「陛下!」亨利希说,「那位侍从可以作证!」
「是真的吗,约翰兄弟?」皇帝语调上扬,望向已经退到一旁的小鬍子侍从。「是的,陛下,」侍从回答,「我看见伊利诺骑士把公爵击倒在地,还把公爵大人平常挂在脖子上的金鍊条缠住他的颈子。」
「你看我的脚跛了,」公爵对皇帝说,「看看她是怎么对我的,陛下!」
「不,在伊利诺骑士还没揍公爵的时候,公爵的脚就是跛了的,」侍从突然这样说道,令公爵表情骤变,从向皇帝呼求公道的哀告转变为吃惊。「而且公爵夫人当时与伊利诺骑士行可羞耻的事,」侍从继续陈述他所看到的,「公爵只是行使他作为丈夫管教妻子的权力,就被伊利诺骑士揍了。」
「什么管教妻子?」皇帝质问约翰,「你是什么意思?」
「公爵掐了公爵夫人的脖子--」约翰话没说完,被公爵转身用双手掐住脖子。「你不要胡说八道!」公爵大吼。
「放开他,亨利希,」皇帝没有走上前阻止公爵,只是语气慵懒地下令。「陛下,」公爵双手还掐著侍从约翰,却转过头再以哀求的语气向皇帝呼告。「已经够了,」皇帝懒懒地一手搔搔头,像是不吃这套,「你找的人证也太烂了。你不知道巴鲁莎就是由你面前那人引见给阿布雷希特的吗?」
「什么?」亨利希在惊讶中鬆了手。「你都不认得他?」皇帝说,「他跟在阿布雷希特身边那么多年,总要有点印象吧。」
怎么会有印象呢?他是一个多高贵的人啊,怎么会记得一个低贱的侍从呢?话说回来,他还真的有些记得大熊阿布雷希特身边有个侍从老骑著骡子跟著他的白马走。难道就是他?他又是怎么变成皇帝的侍从的?
(阿布雷希特带著汉堡的援军回到已经解围的苏普林堡,皇帝带著仪仗队和巴鲁莎出城迎接时,公爵并没有跟随,因为公爵不屑为一个边境伯爵接风,而且阿布雷希特还是他母亲幼妹的儿子,对萨克森公爵这个位子也有声索权,令他感到十分不快。既然他当时没有跟著皇帝出城,也就不会看到皇帝是怎么请阿布雷希特把侍从让出来的经过,更遑论注意到一个老是被皇帝叫做约翰兄弟的侍从跟狼人们总是走得特别近。)
「这件事我会处理的,」皇帝的声音把发愣的公爵意识拉回现实,「你先回去休息吧,亨利希。」
「陛下,」公爵呐喊道,「你要对那白狼轻轻放过吗?」
皇帝原本半瞇著眼,一副慵懒的表情,突然瞪大眼睛,彷彿有火要从眼睛喷发出来,「轻轻放过?」他瞪著他的女婿,提高音调质问道,「你觉得我对我的救命恩人,因为她的族人误猎一头鹿,责备她一顿,这样叫轻轻放过?你觉得我对你妻儿的救命恩人,同时又冒犯了你,是要轻轻放过,还是重重惩罚?我有说不处理这件事吗?你要我下令杀了白狼吗?不行,在我还没下令怎么惩戒她以前,你不可动她。她是我的人,你皇后的骑士!要惩治她,我说的算,皇后说的算,你说的不能算!」
「陛下!」
「回去吧,」皇帝指著门,「我明天就会处理这件事。现在你且去休息,不然我怕你明天又在傻狼面前吃亏。」
「明天是礼拜日,陛下!」
「安息日不可做工,是吗?」皇帝语气略带嘲讽,「我都让傻狼在礼拜五结婚了,你怕什么?教会?在我们还没把教皇送回罗马以前,一切问题都是小问题。现在,请你回去休息,我儿。这样你才有力气应付明天的答辩。」
公爵闭上眼,从鼻子呼气,鬆下紧绷的肩膀,向皇帝弯下背行礼,转身一跛一跛向门走去。约翰正要走去搀扶他,却被皇帝叫住:「约翰!」
「是,」约翰停下脚步,双手悬在半空,脸转向皇帝回应这么一声。(而公爵摆过脸来狠狠地瞪著约翰。)
「你找普洛克(Plock)来扶公爵,」皇帝吩咐道。约翰恭敬地低头回答,「我来扶公爵就行了,陛下。」「不,」皇帝命令约翰,「你离公爵远一点。不要惹他生气。快去找普洛克来。」「是,」约翰迅速从门口退出去。
「不必那么麻烦,陛下,」公爵回过头说,「我自己走就行了。」「不,」皇帝坚持道,「你再等一等。普洛克马上就来扶你。瞧,他来了。」一个留有落腮浓鬍的男人走进来,向伯爵行鞠躬礼,上前一手搂住公爵的腰,另一手抓住公爵的左腕,把公爵整条左臂圈上他的颈后,慢慢带公爵走出门。
从刚才就一直保持沉默的皇后看公爵的背影在门外消失,便从更衣室门口走到床边,稍微抚了一下床单,说,「该睡了,洛泰尔。」皇帝叹了一口长气,默默回到床边,与皇后和衣睡下。
*
「你们出城就带这些?」阿布雷希特问。「对,」灰狼洛奇点点头。
在床上摆的是两把剑,除此之外再没其他东西。
「好吧,」阿布雷希特点点头,「你们三个当初见我也是什么都没带,」然后他把手放上眉部,半遮闭上的双眼,叹出一声「唉,」他在感叹这三头当初看来十分团结的战士小队,就因为约翰的嘴而分崩离析。他乃听信布鲁托的说法,而布鲁托也向他坦承确实伤害了洛奇,这让布鲁托的说法相当可信。约翰在他心中就是这样的杂碎,布鲁托对约翰作为的形容他还觉得太温和。
都是约翰的错。
「我会带上寒风,」巴鲁莎在佳楚德以及包括布鲁托在内搬行李的侍从与仆役离开阿布雷希特所住客房后不久就甦醒了,她一这么说,阿布雷希特与洛奇都往右撇过头来看著她。她则双脚着地坐在床边,一手握住床上那把皇后赐给她的红石宝剑,据说那是皇帝洛泰尔讨伐波希米亚使用过的,她很宝贝那把剑。「你要把它带进森林?」阿布雷希特问道,「你不是说它怕狼,唯独不怕你?」
「他终究得习惯跟我们相处。他是我的马,而我是狼群的一分子。」
「你要让他成为伊利诺人,对吧?」阿布雷希特咧著嘴笑,觉得自己说了全世界最好笑的笑话,但他发现两双金色狼眼望过来的眼神是严肃的,「老天,」他双手抓住自己的脑袋瓜,「你们是认真的。」
「寒风不只是一匹马,」巴鲁莎微微点头,「他还是我的朋友。」
第二十九章(2016/8/23)
被仆人普洛克搀扶著要往房间移动的公爵在走廊上遇见不知从哪裡来又要往哪裡去的公爵夫人。公爵夫人原先冷著脸望著公爵,忽然又露出微笑,温婉地说,「你回来啦,」她柔声招呼著她的丈夫,儘管她丈夫一隻脚是她踹跛的。「我不是一直都在这裡吗?」公爵也微笑回应,儘管他刚才呼了他妻子一巴掌,后来又掐了他妻子的细颈。公爵夫人走上前,从大鬍子普洛克的手接过公爵的左手,「你可以回我父亲那裡了。谢谢你,普洛克。」大鬍子普洛克向公爵夫人鞠了个躬,「这是我应该做的,夫人,」然后普洛克就转身走了。
公爵收起他的假笑,扭头问站在他左侧的妻子,「如果你没遇见我,你会往哪走?」
「我一定会遇见你,」公爵夫人保持微笑回答,「因为我本来也要往我父亲那裡去。」
「哼,」公爵把他的脸往右别开,「你要替你的母白狼情人辩护,对吧?」
「听好,亨利希,」公爵夫人说,「我是你的妻子。伤害你就是伤害我。我不希望白狼受我父亲信任的时候你去我父亲面前讲她的坏话,那样做对你不好。」
「难不成他会废除我继承的资格吗?」
「他不能这么做。可是你如果保持这样要强的个性,他死后你可能没办法得到他的王冠,」佳楚德眨著她棕绿色的眼珠,向她的丈夫陈明利害,「你所有敌人会团结在一起对付你。我父亲手下被你得罪的人也不会支持你。还有阿布雷希特……」「不要提那人的名字!」亨利希发出愤怒的低吼,打断他妻子的劝谏。
他们互望一秒。佳楚德坚定地注视她丈夫的双目说,「你觉得你现在该提防的,是一个爬升太快,但永远不会被其他贵族接受的怪物,还是你母亲姐妹的儿子,对我父亲准备要让你继承的萨克森也有声索权的阿布雷希特?」
「你这是什么意思?」
「当你踞肆待人的时候,阿布雷希特在做什么?」佳楚德顿了两秒,深吸一口气,再说下去,「他在善待每一个他能善待的人,不管他是骑士还是侍从。你看到白狼了吗?你看到他身边的狼人侍从了吗?」她伸出右手,轻抚她丈夫的脸,「不要小看每一个能成为你助力的人,也不要仇视她,」她口中的「她」,很明显指的就是巴鲁莎,「我很抱歉说了那些没有凭据的话伤害了你。可是,亨利希,」佳楚德说,「你最大的敌人不是白狼,是史陶芬家族,再来才是阿布雷希特。白狼根本不能算是你的敌人。只要你把她争取过来,阿布雷希特算什么?」
亨利希皱著眉说,「你该不会想说你刚才跟白狼亲热都是为了我吧?」
「怎么不是?」佳楚德发出轻笑声,「告诉我,我们养狗是为了什么?」
「为了狩猎,」亨利希很快回答。
「那么我善待巴鲁莎像对我们养的好猎犬那样,难道不是为了一场更大的狩猎吗?」
「你不会和猎犬亲热,」亨利希斜视著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佳楚德挑挑眉,说,「你确定?」
同一时间,远在东弗兰肯,趴在床上昏迷的施莱歇尔男爵在沉睡中发出一声惊叫而甦醒,所有服侍在旁的仆从赶忙围了过来。「这是哪裡?啊……」男爵卡尔因为用力说话动到了背上的剑伤而发出呻吟,再次说话时音量已小了许多,「我在哪裡?我昏了多久?」他问。
「你在希德勒村村长家裡,爵爷,」一名仆役回答。「希德勒村?」男爵想起他的私生兄弟约瑟夫就是在这座村庄蒙难,然后被一间农家给救的。「现在什么时候?」男爵问仆从。仆从回答,「接近午夜。」
「日期?」
「十二月五日。」
「我昏了两天……」男爵喃喃唸著,再抬眼,说,「把施莱歇尔家的骑士都找来。快。」
等到施莱歇尔家的骑士都到了,男爵便开口问道,「谁说要撤出安哈特的?」
十数名骑士有的低下头,有的望向其他人,有的四下张望,彷彿男爵问的那人散布在空气中。终于一名黑髮骑士向前站了出来,说,「是我,」但他听见另一道声音跟他说了一样的话。大家都把脸转向另一位说「是我」的骑士,那是金髮的亨弗里。原本保持沉默的褐髮阿图尔叹了口气,也站出来说,「不,不是他们两个。这都是我的主意。」
黑髮骑士急切地大声说,「不,不是他们。是我!」金髮的亨弗里说,「别闹了,寇特。我们当时都看见是谁下令撤退的。是阿图尔把我的主意付诸实行的,男爵,」亨弗里向床上坐著的男爵单膝下跪,右手放上心臟,「请单单追究我的责任就好。」
男爵轻声笑了几下,紧绷严峻的表情缓和下来,「放轻鬆,三位,」他忍著背上的伤痛轻声笑著,「我都不知道你们是争著认错还是抢功劳了。的确,」他敛起笑容,「撤退不是我会做的决定,但是,我知道那是当时最好的决定。所以,」他闭上眼,向众骑士低头,「感谢你们当时的正确决定,拯救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宝贵性命。」
黑髮骑士寇特突然在已经单膝下跪的亨弗里身后弯下右膝,高喊「誓死效忠爵爷!」其他骑士纷纷跟进,曲起右膝向床上的男爵跪下,齐声高喊,「誓死效忠爵爷!」
*
苏普林堡,早晨,礼拜日,十二月六日,王室带著众多贵族与仆役前往圣彼得与保罗教堂参加礼拜。当贵族的队伍走过城内主街,围观的民众发现原本会一直走在皇帝夫妇身边的白狼不在那裡。在围观的喧嚷之中,流传著各种议论。「希奇了。白狼跑哪去了?」「听说她昨天被国王骂了一顿。」「你怎么知道?」「我侄子是城堡裡的仆役,他在国王的花园裡看见的。」「胡说。白狼怎么可能会被骂?」「你就不会骂家裡养的狗?」「谁会养狗?」「你不养狗?」「我自己都吃不饱了还养狗?」
而白狼此刻牵著她的白马寒风,与她的丈夫灰狼洛奇并肩跟随安哈特伯爵的返乡行列,避开主街,向城北门走去。
「终于要离开这座混乱的小城了,」安哈特伯爵大声感叹著。「苏普林堡是混乱的吗?」白狼巴鲁莎出声问前方骑马缓步行进的伯爵。「难道不乱吗?不晓得有多少贵族跟巴本男爵一样,向萨克森,巴伐利亚,与士瓦本同时宣誓效忠。他替士瓦本谋画杀害凯撒,又要在死前说自己对不起凯撒与公爵。我还真不知道他对不起的是萨克森的凯撒,士瓦本的凯撒与他的公爵,还是巴伐利亚伟大的公爵大人。」
「别再说了,爵爷,」已经化为人形的布鲁托走在伯爵的马旁低声劝道,他人形时相貌相当瘦削,且比他狼人型态还矮一颗头,只有那头浓密如狗毛的黑髮才能让认识黑狼布鲁托的人勉强联想到他的毛色。「我才不怕,」伯爵还是大声嚷嚷著,「不管是士瓦本兄弟还是巴伐利亚兄弟,他们有多少耳朵在城内,就让他们听吧。反正我也从来不会讲他们什么好话。就让他们听到生气吧。他们拿我没办法的。」
他们走到城门前,卫士问伯爵,「你不随凯撒去做礼拜吗,伯爵?」伯爵回答,「我要到树林裡,和我的狼人朋友们敬拜上帝。」
树林裡那片空地,昨日上演对同性恋与外人的批斗,今早又是另一场批斗:灰狼长老娜西塔召集族人,提出罢免酋长的动议。「你这是什么意思,娜西塔?」沃坦长老在族人的沉默中朗声质问他们的巫医长,「当初说伊利诺酋长适任的是你,现在说她不适任的又是你。」
「我的治疗术一直以来都比占卜高明得多,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娜西塔抬高她的长鼻与下巴,冰冷地发表她的声明,「而关于约翰那个预言,我知道我不过是凑巧猜中。在那之后我有多少预言是应验的?」
「关于巴鲁莎的预言就应验了,」沃坦说。
「可是那是关于那位巴鲁斯的,」娜西塔激动起来,简直是气得发抖,「而你们都不相信我的说法。」
黑白相间的老雄狼摇摇头,「你说过那预言是关于巴鲁莎……」「那是伊利诺说的!」娜西塔尖声嚷著打断沃坦的话,「她一直对你们说我那五枚符文指的就是巴鲁莎,可是我从来没这样讲。我说的是復仇的机会即将到来。」
「然后巴鲁莎就出现了。」
「但是预言指的不是巴鲁莎!」
「够了,不要再讲预言了!」最年长的长老弗丽嘉已受够两位长老之间无意义的争论,大声吼了出来,吓得两头老狼赶紧闭嘴。然后弗丽嘉转向前任酋长,年纪最轻的「长老」,巴鲁莎的父亲芬利斯,「当初是你推荐伊利诺继承酋长之矛的,芬利斯,」她问,「你有什么看法?」
芬利斯就坐在三大长老的身边,谦卑地低头贴耳听他们的谈话。此时他抬起头来,望了望坐在他对面低著头的雌性狼酋。被当初大力支持她当酋长的巫医长否定的狼酋伊利诺,一直低头看著她盘起的双腿前横摆在地的酋长之矛,不敢抬头看芬利斯。她知道芬利斯对她昨天的表现相当失望。她对布鲁托的攻击完全是因为嫉妒心与恋慕被践踏的报復心所致。她等待芬利斯发言。她等待他宣判。
「各位应该还记得,伊利诺是一位好斥堠,帮助我们避开过不少疯狂的骑士行列。我也因此在那时决定将酋长之矛传给她。可是她这两个月以来的表现,证明她只能是一位好斥堠,不是一位好酋长,」芬利斯直盯著伊利诺。伊利诺还低著头,但能感受到芬利斯的瞪视。她听见老白毛狼男说,「因此,我提议废止伊利诺的酋长职权,另外挑选人才,将酋长之矛交给他。」
围成圈的族人们开始热烈地讨论。忽然有人高喊道,「把布鲁托找回来,让他当酋长!把巴鲁斯找回来,让他加入我们!」那是黄毛狼男尼克,族裡的二把手,伊利诺的妹婿,布鲁托儿时最好的朋友。
「让约翰回来!」在一片喧譁声中,尼克的妻子卡拉也充满激情地呐喊著,「他是施莱歇尔家的私生子。他可以带我们回到故乡!」她只想著让她心目中的狼族救主回来,并不关心她的酋长姐妹。
「巴鲁莎不是伊利诺骑士吗?」一名今年春分才经歷过成年礼,已经可以在会议中发言的狼人少年也大声喊出他的意见,「就让她当我们的酋长吧!」
少年提出的这个意见比尼克夫妇分别提出的可疑建议还要顺理成章,族人们纷纷以嚎叫表示同意。「巴鲁莎已经是我们的领主了,」芬利斯在群众的嚎声中竭力喊著,「伊利诺的酋长得选择他人,并经过她同意……」「嗯嗯嗯嗯嗯!」一阵凄厉的马嘶声从空地外围的树林间传来,将狼族的纷扰打回平静。伊利诺的狼人与狼循声望见穿著绿色男装的伊利诺骑士「白狼」巴鲁莎牵著一匹白马沿树林间的小路走来。她牵著的白马看起来有些焦虑,不断从鼻孔喷气。她则不停轻拍白马的大鼻樑,细声安抚它。
白色种马寒风完成了或许其他马这辈子不可能完成的一项成就:随著他的狼头主人走入一群狼头怪中间。
而上次有马进入伊利诺人中间的时候,是在十三年前施莱歇尔男爵的骑士们进入伊利诺村大肆屠杀之时。
白狼骑士站在族人们围成的大圈中央,确定白马不再发抖,便环视她四周的族人们,大声宣佈,「我作为凯撒任命的伊利诺骑士,如我的父亲芬利斯长老所说,我拥有任命伊利诺村长的权力。现在我在这裡宣告,你们不能收回伊利诺酋长的矛,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丈夫阿弗雷道夫骑士洛奇也不允许。被伊利诺酋长提议逐出部落的布鲁托也告诉我,我们需要她继续领导我们,所以,」巴鲁莎一手抓著马嘴上的缰绳,另一手捏住坐在她面前傻傻盯著她看的杂色毛狼女左肩,示意要狼女酋长起身。伊利诺照办了。巴鲁莎又蹲下捡起酋长之矛,把矛推到女狼酋怀裡,并大声说,「没有我的同意,谁都不能说要夺走伊利诺酋长的矛,就算是我的父亲也不行,弗丽嘉长老也不行。我说,伊利诺是我们的酋长,除非她死,或是亲手将矛交给她的继承人,否则谁都不能说要废止她的酋长职权,」巴鲁莎说完,左手还捏著缰绳,突然就向伊利诺行单膝跪拜礼,右膝碰地,右手心贴上胸口,抬头仰视女狼酋。「你在做什么,巴鲁莎?」狼酋伊利诺弯腰抓住巴鲁莎的双肩想把她拉起,巴鲁莎右手反抓住伊利诺的左手腕,「我将族人们交给你管理,你不能拒绝。」
伊利诺深深吸气,左右来回摆头,「那晚我就在你丈夫附近,可是我只是看他被砍。你被小刀戳伤脚,我也没帮你。」
「那都无所谓了,」巴鲁莎说,「现在我们要团结在一起。布鲁托会跟著安哈特伯爵,他俩都会帮我们的,」说完,她放鬆上仰的后颈,向自己刚才的来向平视。伊利诺循她的视线扭头一看,只见安哈特伯爵在另一名狼人骑士洛奇,披著熊皮的巴鲁斯,以及一名黑髮人类侍从的陪同下,出现在林间小径通来空地的入口。
伊利诺站在上风处,嗅不到伯爵,他的两位侍从,与洛奇接近的味道。但她特别被那名黑髮绿眼的瘦削侍从吸引。她其实根本无法确定,但她认为那名黑髮青年就是那个让她由爱生恨的雄性。她抓著矛向黑髮青年走去,走过了刚才狼群为牵马的巴鲁莎让出的一条通道,一直走到那人面前,「你是布鲁托,对吧?」她问。黑髮青年沉默地点点头。
她抱住黑髮青年,痛哭起来。
圣彼得与保罗教堂的祭坛前,凯撒洛泰尔在耶稣受难像下双膝下跪,在额上,胸口与双肩画了十字,闭眼祈祷著。皇后也在他身边跪下。凯撒与皇后的独生女佳楚德则抱著她的独生子亨利希站在她父母身后,眼神恭敬地垂下注视他俩的背影,她身旁则站著她的丈夫,巴伐利亚公爵亨利希.冯.韦尔夫。在公爵身边,又站著公爵的幼弟,温顺的韦尔夫,抬高脸面仰望著耶稣像。
主啊,我感谢你。你毁坏我兄弟的谋画,却也免了他的罪。我必定竭尽全力劝诫我的兄弟回归正途--他这么在心中默唸著,并在自己身上虔敬地画了十字。
约翰也仰望著耶稣。自十三年前上帝在他身上显示神蹟,他便无时不倚靠著上帝。他行事谋画靠所谓智谋,但他自己清楚这些「智谋」其实一点也不聪明,它们能成就都是因为上帝应许。十三年,世事多变,当初该为伊利诺村屠杀负责的人几乎死尽了。重点已不在復仇,而在让伊利诺人在这场混乱中争得一席之地,荣耀,还有他人的尊敬与惧怕。没错,惧怕,让那些视平民如杂草一般加以践踏的贵族们在遇到伊利诺人,或进入伊利诺村的地界时,得好好考虑自己是否该把自己的恶行加在这群善战的民族身上。明天,他就要随王族迁往纽伦堡了。未来还会再发生什么事,他不清楚,但他绝对要继续尽他的力守护所有的伊利诺人:为了塔西娜的信任,为了芬利斯一家对他的照顾,为了他对伊利诺村的亏欠。
他的视线从耶稣像往下移,刚好与两位狼人侍从对上眼。他们是弗雷奇与格利,凯撒说要好好培养成为骑士的灰狼兄弟。他看著他们兄弟俩,彷彿看见伊利诺村未来的希望。两位狼人少年也对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报以灿烂的露齿笑容。
为了伊利诺--当初与三位狼人伙伴一起许下的诺言还在,而今「三狼组」因他的挑唆而有了嫌隙,想必三位也不会再无条件的信任他了。事情就是这样。就算他失去所有人的信任,甚至死后下地狱,为了伊利诺,他什么都愿意做。
就算要把灵魂交给恶魔,他也愿意。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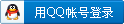












 发表于 2016-7-31 19:18
|
发表于 2016-7-31 19:18
| 




 发表于 2016-8-27 16:53
|
发表于 2016-8-27 16: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