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世界: 【Dragicland】 头衔: 记录世界的探险家
|
展开以显示更多内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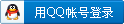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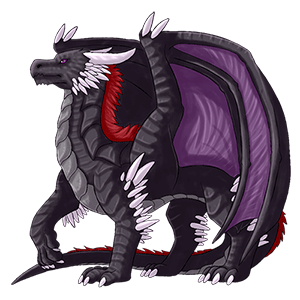
 发表于 2025-3-19 23:22
|
发表于 2025-3-19 23:2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