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世界: 【烈火流星】 头衔: 姊姊的妹妹(?)
|
展开以显示更多内容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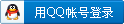















 发表于 2022-8-29 22:14
|
发表于 2022-8-29 22:14
|  (X
(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