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羽·凌风 于 2022-11-10 08:22 编辑
当初每日挑战画到恐怖鸟的时候就说在写的,一个古生物物种被发掘出来的故事(?)
天河岛广袤无垠青绿连天的旷野上,一辆飞车正贴着地面极速奔行。草地上没有路,车身便悬浮于青叶和碎石之上,扬起连串的浮土。
那车上坐了两个人,一人悠哉地半躺在驾驶座,正捧着手机刷短视频,看得满脸乐呵;另一人则侧俯于副驾位,双目失神地凝视车外的荒原风景,看那白花花灰扑扑蓝幽幽青茫茫的天地好似刚下过雪。清风自挡风玻璃外侧涌入车内,即使经过风罩的衰减,仍呼啸连连地砸在两人脸上。
看手机的人在换视频的间隙随手理顺飘飞的青白头发,同时又往下缩了缩,身后一对青羽蓬松的大翅膀跟枕头似的拢在脑袋两侧,那样子好生安逸。相比起来另一人可就悲惨多了,他发色棕红,皮肤也比前者深得多,没有天生自带的枕头、也无心思享受旅途,紧绷的神情显示他内心底所有的精力都在和晕车做对抗——他显然不是个“云洲人”。
“需要我开慢点吗?”那看手机的云洲羽人注意到同伴的状况,翻动翅膀撑起半个身子来问。
晕车者有气无力地摆摆手,从喉咙深处发出两声哀叫:“还要……多久?”
“快了,”羽人抬手指向前方不远处的青白土山,“营地就在那边的山谷里面。”
闻此,晕车者发出一阵脱力而悠长的叹息,转背去找个舒服的姿势缩着继续哀嚎。羽人也回头重新玩起手机来,并不忘在心底里嘀咕一声:切,坐个车都能晕成这样,弱小的匍匐者。
说实在的,如果不是工作需要,他这个云洲羽人真心一点也不想和地面上的匍匐者共事。那些家伙矮小愚钝、肤色晦暗,身上总是带着一股来自黑土地的泥腥味,让人光是看一眼都觉得浑身不舒服。但也正是那片让人不悦的黑土地,比云洲的青白浮土更加厚重更加致密的黑土地,才能保存下足够多来自远古的信息。
而他,龙鹫神殿的古生物学家轻羽,就很需要那样的信息。
被同行旅伴一打岔,看短视频突然变得没什么意思了,他放下手机,翻开神殿同事发给他的文件,心想着干脆再熟悉熟悉一会儿将要面对的工作好了。
文件里简洁描述了龙鹫神殿在天河岛远山中的一项重大发现:一个多月前,有农人在干河谷里采伐时掘出了个埋葬着大量人骨的深坑,白花花的骨头从灰土地里面露出来,俨然一座可怖的坟场。农人立即报了警,待警方检测后却发现那并不是新鲜的人骨,其距今早已有千年万年以上,显然不属于他们管辖的范畴,于是通知了轻羽所在的龙鹫神殿——也就是云国考古与古生物研究所。
这着实是一项了不起的发现,毕竟云洲的泥土疏松潮湿,那高高的云端又常年沐浴着温润的阳光,这样的环境最适合食腐生物生长,无论什么人骨兽皮龙鳞都难以在云洲的土地上存留数年为记的时光,更别提千百年了。只有在背光的阴坡和干旱的谷地,动物的尸骸能够躲过时间的侵蚀,保存下来。
轻羽看着文件中附的照片,看着那上面露出白云土地的森森长骨,确实很像羽人的股骨,不由得啧啧感叹。不容易啊,云洲的考古学家们想要发现点远古生灵和古代文明的遗物,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所以云国的考古学很差,差到每当有点新发现,还得请地面上、由那片不详的黑土地教育出的原人考古学家来做现场指导。啧,轻羽瞥了一眼仍然在哀叫的原人同伴,号称是北若兰的著名古文明学家呢,他不由得哼出声。这个一到云洲就水土不服的匍匐者,最好是能够帮上忙。
飞车持续在山野里行驶一个多钟头后,于晌午时分抵达了行程的终点。那是一处清秀的谷地,呈蘑菇状的云山由两侧夹着一条业已干旱的河川,龙鹫神殿的野外营地就在向阳的山坡上。
营地的简陋土门缓缓开启,驻守于此的龙鹫神殿考古学家鸣泉早已站在门后驻足迎接。他挥舞宽大的湛蓝翅膀,引导飞车降落在经历过火焰烧灼、稍加硬化的泥土上。
“可算等到你们了,轻羽教授,熙教授!”车还没停稳,他就急不可待地迎上前来,用手轻拍飞车的挡风罩,连连招呼,“我寄给你们的资料都收到了吗?你们有什么看法?”
轻羽过去和这个主攻古文明发展的鸣泉有过合作,那是个工作起来风风火火的主。此刻他看到对方兴奋得头发飘舞、好似在太阳底下烧,不禁觉得有些头痛。他扭头瞥了一眼同行旅伴,那位叫熙泽的原人考古学家整个身子都蜷缩在飞车宽大的座椅里面,双目紧闭,似乎还没注意到车已经停了。
“怎么样?我现在就带你们到挖掘坑去?”而鸣泉显然没意识到来人的状态不佳,待车熄火、风罩消散后,他便立即拉开车门,青蓝眼睛里满是激情。
轻羽从舒服的大座椅里立起身,抬起翅膀尖指了指昏睡的原人,示意这里有人不能工作呢:“别急,地面人坐不惯飞车,还不能动哦。”
“啊这……”见状,鸣泉的兴致立即熄灭了大半,他附身搀扶,巨大的蓝翅膀靠在东倒西歪的原人脑袋边上,毛蓬蓬软乎乎的看着可舒服了。他领着远道而来的原人教授往营地的方向走,说话的声音也变得软绵绵轻飘飘了些:“要不,我们先吃饭吧,下午再去现场。”
听到这话轻羽不由得笑了,看这些地面人吃云洲食物是一件很愉快的事。他整理好车上的文件,乐呵呵地跟在同事身后走进营地里的简易餐厅。
云洲随处可见蓬松到容易塑形的云白土,云洲人也各个都是玩泥巴的大师,不仅擅长空手搓出雕塑来,拿着一套建材工具后更是寥寥数人就能搭建起土墙围筑的营房。简陋,但在野外应付应付倒也足矣。而据神殿里的传言,眼前这个先行赶到的鸣泉教授还是个一刻都闲不下来、就喜欢捯饬折腾的人物,轻羽一看餐厅的样子,连连感叹他果然是名不虚传。
这个刚诞生还不到半个月的野外营地看上去远比它的年龄要精致,三栋分别用于住宿、办公和餐饮的平房围成了云国建筑常见的三棱柱结构,青白色的软土墙体亮得像鸣雷的积云。楼宇的墙上爬着青瓜藤、楼间的地里种着甜豆苗,那叶嫩得好似晴日落在轻云后,那花艳得堪比夕阳沉进天湖里。
“好家伙,搞得不错啊。”轻羽随手摘了一截嫩藤尖,放自己嘴里细细咀嚼。抿甜,不愧是天河岛上长出来的甜瓜颠。
“全靠那些本地农工帮忙啦。”鸣泉指着饭堂里几乎占了一半多的农工,笑道。
这话没错,像这种做野外工作的神殿,自己编制内哪有那么多人手可以干苦活,便常会在工地附近招募民工做帮手。一些更加深入荒野的研究所甚至还需要招收向导和猎手,比如研究生态学的狩猎神殿,网上常能看到他们工作的视频,尤其是在抓捕样本之前那些当地猎人还会围着营地大门口的飞龙神徽跳一段祭祀舞,打趣得很。龙鹫神殿的营地就没那么有趣了,只有一群膀子粗得能抗起两大麻袋云土飞上五公里的壮汉,在一边哼着祝酒的曲子、一边举着盘子向盛饭的农工吆喝,“再来点!甜瓜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干活!”,然后满足地端着几大碗看起来含糖量就很高的果蔬回到座位上。
说到饭菜,轻羽看着鸣泉让餐厅准备好的大桌子饭菜,一上午的舟车劳顿立即消散了大半。看看这些诱人的食物,这些鲜嫩欲滴的青菜叶、肥硕多汁的香瓜瓤、还有香脆可口的豆角干……哦,瞧那豆角干啊,颜色棕黄深沉、结构纤维分明、闻着还有股干燥浓郁的蛋白质香气,很像野蛮的地面人最爱吃的肉干。
“尝尝吧,云洲特色料理。”轻羽兴起,指向那盘“肉干”,微笑着对熙泽说。
好不容易从晕车的不适感中恢复过来,熙泽早就饿了,听到主人家发话,急忙叉起一块看起来油嫩厚实的“肉干”,满心期待地送进嘴里。然后他表情凝固、愣住半晌,才弱弱地说道:“这……不是肉啊?”
对对对,就是这个,匍匐者吃云国食物时最好玩的反应!轻羽忍不住笑得那是前仰后合,惹得鸣泉也情不自禁地咯咯哂笑起来。
餐毕,新到的两人在鸣泉的带领下于住宿区入住,小憩片刻躲过云洲最烈的午后阳光,再跟着鸣泉来到位于营地外的挖掘场地。已有不少人在挖掘坑中忙碌,大多是龙鹫神殿的技术员,以及一些前来实习的学生。当地农工不会干考古学家们的精细工作,用熟了大型农具和重物的手拿不惯小土铲和小毛刷,便三三两两地聚在挖掘坑边围观,时而搭把手帮忙把清理出的土屑运走。
那挖掘坑足有二十米见方,内部根据考古的习惯用土墙围出了许多方格,越是靠近中心插着越多标示文物的旗子。轻羽来到坑边,探头望去,只见那坑里密密麻麻尽是骸骨,云之民的骸骨,中央地带一具挨着一具整齐排列、边缘则满是混乱堆砌的碎骨,像极了古时候部落酋长或者战国君主的祭祀坑。嚯,还真和报道上说的一样,是个“坟场”。
这样骇人的祭祀坑,在原人的古文明里很常见,没什么好奇怪的,穷凶黩武的匍匐者嘛。轻羽斜眼瞟了站在旁侧的熙泽,这个来自地面的考古学者确实一脸淡定,甚至还饶有兴致地观望这一地白骨。但是这样的场景在云之民的历史中却并不常见,云之民习惯用小动物、雕塑或是装饰鸟羽的兽骨作为献给神明的祭礼,即使是在人命最不值钱的战国时代,以人为牲依然是最凶残的暴君才干得出来的恶行。能在云洲的土层里发现这么一个罕见的文明遗迹,轻羽可以理解为什么作为古文明研究专员的鸣泉会如此激动了。
只是……“这些和我这个古生物专业的有什么关系?”
轻羽面向鸣泉问道,耸搭着双翅,满心不解。他说话时,原人已经愉快地跳下了挖掘坑,屁颠屁颠地跑到正在挖掘的技术员面前去打听细节了。看吧,他指着原人的背影向自己的异部门同事示意,这地方是你们这些古文明学者的专场才对吧。
鸣泉抬手捋着半长不短的青发,没看人影忙碌的挖掘现场也没管已经和技术员打成一片的原人顾问,而是领轻羽来到工地旁附近的办公小屋,一脸神秘的模样。那小屋宽大平坦,没有隔出内室,三面围墙一面透风,门比停放飞车的室内车库门还大,里面整整齐齐摆了一地贴好标签的骸骨,这是用来存放和研究文物的仓库。
“给你看个东西。”他说,从地上拾起一个标注了33号码的口袋。薄而坚实的透明塑料袋中赫然装着一截足骨,和云之民的足骨很相似,完整的骨头上有几道合并的痕迹,但长度比云猴子的脚掌还夸张。轻羽接过口袋细细端详,这足骨没有趾行野兽那种好似蓄力弯弓的足弓结构,确实是云之民的骨头。
“这是什么?畸形的人骨吗?”轻羽问道。
鸣泉点点头,想了想又摇头,指着挂在墙上的挖掘坑地图一个角落说:“33号在这里,另外我们在42号和47号位置也发现了类似的骨头,我们这里的人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人骨。至于他们是什么样的畸形,和人祭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我请你到这儿来的原因。”
原来如此,古文明不是他的强项,但研究骸骨、尤其这种没人见过的骸骨,倒是他的专长。轻羽欣然,他乐呵呵地捡出方才鸣泉提到的编号,瞧见那些口袋里果然都装着看起来像人骨但比例又似乎有些怪怪的畸形骨头。
粗看过去,这其中不仅有偏长的足骨,还有粗大的盆骨和极细的臂骨。有意思,没想到一个人祭坑里还能发现这样的东西,轻羽捧起骸骨,微笑着,好像,已经可以看见论文正在远天太阳的光辉里向他招手了。
那天轻羽在文物仓库里待到很晚,他把畸形的骸骨全都整理好,还从人骨堆里挑拣出了好些鸣泉没能分辨出的怪骨,那些更长的胸骨和略尖锐的头骨。这些畸形骸骨散布在祭祀坑四周的各个角落,看上去确实和人祭关系重大的样子。
他一心一意地整理,直到西天的太阳快要隐没在昏黄的云湖里,直到外面嘈杂的工人往来的声音逐渐散去,他才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对于云之民来说,太阳落下地平线后还在天穹底下游荡可不是什么舒适的事情,于是轻羽急忙放下工作,追上了最后一批离开工地的技术员。
好在工地距离营地很近,可怖的夜幕还没有来得及占据眼下的天地,在外疾行的人就已回到了充满安全感的室内。轻羽刚走进食堂,就见鸣泉探着身子伸长手臂,向他打招呼。
“抱歉,熙教授说一天没到吃肉,身子感觉有点虚,我们就自己先回来了。”
鸣泉说这话的时候,还笑盈盈地看着坐在身边的熙泽,这个自称没肉吃的可怜原人正抱着一盘看起来就很贵的香瓜焖禽肉大快朵颐。注意到被落下的同伴回来,熙泽抬起头,嚷嚷着没想到云洲的肉菜也不赖嘛,嘴里包着食物连话都说不清楚。
云之民可不像野蛮的匍匐者,没有这种无肉不欢的追求,轻羽撇嘴,照例点了份天河岛特产的喷香甜瓜,真想不通又柴又腥的肉类到底哪里比高糖细嫩的蔬菜好吃。但他现在没空思考食物的问题,他的脑子里还有个比菜和肉更复杂更难解的谜。
“鸣泉,”轻羽咽下一口瓜瓤,感觉终于从下午的忘我专注中回过点神来,问道,“关于祭祀坑,你们那边研究出来点什么吗?这是什么时代的坑,结构什么样之类的?”
虽然描述不怎么专业,但这可是一个直指当下工作核心的问题,鸣泉不禁稍微坐正,和开组会一样严肃了起来:“这个祭祀坑的具体时间还无法确定,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在部落时代,甚至更早。坑里有一些散落的木制工具,保存得不太好,只能大致判断是部落时代早期的样式,也就是距今十万年左右。”见轻羽点头,他接着说道,只是谈吐间显然没啥底气,“至于结构,那个年代的遗址很少,只能推测可能和太阳祭祀有关系,中央是最重要的祭品所以排列最整齐……”
“我觉得这比较像陵墓。”这时候一直埋头大吃的熙泽突然出声打断了鸣泉的话,嘴里还包着肉沫,“我见过好几个上万年历史的原人墓葬,和这个构造几乎一模一样。”
“什么?”鸣泉没听明白。
熙泽想了想,尽量用浅白易懂的词汇给这些考古学水平怕是和大学生差不多的云洲人解释:“墓地,尤其是原始社会的墓地,经常就是像这样,把酋长和部落精英的尸体放在中间,周围围上一圈陪葬,弄得跟祭祀一样。如果陪葬品是动物,就会和这个坑里的一样全剁碎了撒里面。”
听到这话,哪怕是多年研究古文明的鸣泉也难以置信地张大嘴,愣了好一会儿才接话:“啊这,也太野蛮了吧?”
“剁个肉而已,哪里野蛮了?”熙泽不以为然,一边说着,一边用龇牙咧嘴的表情从鸡架子上扯下一大块肉,看得鸣泉是一脸嫌弃。
而提出话题的轻羽则全程听得云里雾里,毕竟他常接触的古生物可不懂得祭奠。不过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思路,那些看上去像畸形人骨的东西,其实是弄碎了导致看不出原貌的兽骨。看到对方笃定的样子,他感觉眼前这个匍匐者,好像确实有点东西。
第二天清早,当东方的天空开始发白时,鸣泉就已经起身洗漱,准备开展一天的工作。他以为自己按照惯例又会是第一个到达挖掘现场的人,直到他进仓库检查时发现轻羽早已在这里——而且正在暴力地把铺在地上的骸骨全都给移到了房间的角落,在中央留出了一大片空地。
“哎,别,我们根据出土位置,好不容易才摆好的!”见状鸣泉大吃一惊。
而轻羽对此不以为意,他摆着手说:“反正都有编号,放哪儿都不影响。你帮帮我,把33号和61号拿过来。”
鸣泉满心疑惑,可依然乖乖照做了。他递出塑料口袋时,注意到空地上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已摆了些骸骨,隐隐约约组成了个人形。那人形很怪,每根骨头都来自不同的位置,长胳膊长腿、连躯干都长得不可思议,怎么看都是一个畸形。
“这是什么?”鸣泉看不明白但大为震撼。
“我在考虑一种可能性,这些畸形的骨头,就像熙泽所说的,是某种动物的骨头,可能是兽神一类的吧。”轻羽则是在心底里为自己的机智点了个大赞,得意地回答,“我刚才发现,这个畸形的上臂骨其实和附近发现的羽神肩胛骨并不能完全贴合,会存在过大的空隙,这个弧度反而和另一个点位发现的畸形肩胛骨更加合适。”他指着地上摆的一对肩胛骨和上臂骨,“还有这个足骨,你看,和畸形的腿骨正好一致,放羽神的腿骨旁边又会显得太大了。”
这回鸣泉大致明白了,地上的骸骨看上去好像确实是那么回事:“你是说,这些畸形骸骨,其实不是云之民?”
“很有可能。”轻羽点头,“但很多畸形骸骨都损坏了,和其它骨头对不上,我还需要更多的样本才行。”
听到这话鸣泉了然,他走到仓库门口,向着挖掘场里的技术员们喊:“中央区域的挖掘先暂停一下,主力挖周边,把那些碎骨头都挖出来,我们的古生物学家有些新发现!”
这时候,太阳已经爬到了山谷的缓坡上面,工地里的考古人员和农工都越聚越多,挖掘坑内人声嘈杂,可鸣泉洪亮的嗓音却能将这些噪音全都压住,好似一道劲风裹着响雷卷在坑里。好家伙,不愧是雷厉风行的鸣泉教授,发号施令时还特地用风魔法形成共鸣加强自己的声音——而且他咋说的来着,“我们的古生物学家”,说得轻羽是头皮发麻,感觉怪不好意思的。
“别这样,别整那么高调。”轻羽埋怨道,不过想到自己作为一个在云洲比古文明学家还难混得多的古生物学家,居然有朝一日能让这些古文明专业的帮自己挖样本,他语气不自觉地有些骄傲。
但鸣泉没听出他的自傲,他回到仓库内,捋着头发说:“你才是别见外,大家都是为了搞清楚这个人骨坑到底是怎么回事嘛。”
说的也是,现在他脑子里能有思路也得感谢鸣泉和熙泽的帮助呢。说到那个原人顾问,轻羽伸直脖子朝挖掘坑里望,在一片和白云土相似的青蓝色人影里并没有看到匍匐者显眼的深色脑袋。他还站起身又确认了一遍,真没有。
“熙泽呢?怎么没跟你一起来?”轻羽问。
“啊……”鸣泉发出一声幽怨的叹息,拿出手机指了下时间,七点半,“原人九点才上班,他们一直都是这样的,习惯就好。”
啧,意思是说这些原人比他们晚上班俩小时,却一起下班?匍匐者果然还是匍匐者,靠不住啊。
在那之后,轻羽一直致力于将所有看起来不像云之民的外围骸骨拼凑起来,尽可能地拼出完整的人形。鸣泉则帮忙打下手,把看上去畸形的骸骨全从人骨堆里整理出来。等到原人活跃的时间,熙泽便来了,随时抬眼都能看到这个匍匐者矮胖的身影在挖掘坑里上蹿下跳,指引技术员们在他判断会有东西的方位进行挖掘。作为来自地面世界的古文明学家,他对云洲人的历史可是好奇得很,尤其是这种五年十年都不定能找到一个的祭祀坑或者战场坑。在他的积极指导下,挖掘坑扩大了好几米,越来越多的碎骨堆被发掘了出来。
除了指导挖掘,熙泽每天都还会来仓库围观“拼图”的进展。外围的大部分都骸骨都被损坏了、只剩些碎骨片,最早发现的臂骨和足骨已是最完整的两块。即使是熟于云国历史上的鸣泉也没有见过哪场祭祀活动有把祭品损坏得如此严重的先例,这看上去即凶残,又有些诡异。
并且随着碎骨片增多,轻羽愈发地确认这里面肯定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云之民的遗骸。畸形骨骼的特征都太一致了,都是相同的细瘦和修长,怎么看都是来源于一个和云之民相异的新物种。可在一些足以把羽神和其他直立神族区分开的细节特征上,这个新物种的骨骼结构却又和云之民相似到了极点。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作为古生物学家,轻羽知道那些整天趴在地面上的匍匐者们有不少亲戚,比爱吃肉的原人还要野蛮的那种,他们的物种演化谱也像个开枝散叶的乱树丛,哪里像羽神,从似野兽的兽神属脱离出来后就是个一柱擎天的独苗,还从没见过长得像羽神的近缘种,这独特性哪里是匍匐者可以比拟的。
直到几天后,在熙泽的指挥下,外围最大最集中的碎骨区域被发掘了出来,大量畸形骨头杂乱地堆叠在一处,看着比中央区域整齐排列的人骨还要骇人。最令轻羽振奋的是,在这片碎骨区里,他找到了和羽神骨骼差异更大的胸骨,和一块相当完整、只有些凿子状伤痕的头骨。看到头骨的那一瞬间,无论这个自傲的古生物学家曾经有怎样的经验和观念,他都不得不承认,这果然不是羽神的骸骨。
那天,在鸣泉和熙泽的注视下,轻羽终于用新发掘的碎骨成功填满了拼图。他注视着地面上这个几近完整的类人遗骸,这个周身长条形的怪物,几乎每一处骨骼的比例都比羽神更细瘦。它的身材瘦长足有三米以上,它的手脚纤细脊背微隆,日常应当是佝偻着爬行,它长有羽神早已退化的小截尾骨,还有它的头骨,它有一颗细节上和羽神相差无几、仅吻部和后脑看起来更加瘦长、仿佛介于长吻的兽神和扁脸的羽神之间的头颅。
这特么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
“这是,云之民的祖先吗?”
此为鸣泉看到怪东西全貌的第一反应,虽然轻羽也很想这么说,但知识和经验都在告诉他那是不可能的事。
“不是,你忘了坑里有什么吗?它们跟我们是同一个时代的。”
对,从这些骸骨的风化程度来看,怎么说也仅有数万年的历史,如果说这些是羽神的祖先,那羽神的演化未免也太快了,这不合常理。而且怪人和羽神出现在同一个乱坟岗里,那么,这只能是和羽神同时代存在过的……“另一种人”了。
“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熟!”熙泽一拍脑袋,嚷嚷道,“这不就像现在的原人和土人吗?长得很像的亲缘物种嘛。但说真的,我还没见过像这样拿亲缘种当祭品的,原人的墓葬里连猿猴都没有。”
啧,刚还在想羽神可没有匍匐者那样的亲戚呢,看到这个莫名冒出来的亲缘种的遗骸,轻羽感到一阵令人不寒而栗的恐怖。熙泽说的对,那么现在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两种“人”的尸骸为何会组成的如此诡异的墓地,这里到底发生过什么?
当天夜里,轻羽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见自己独身一人走在天河岛的荒原里,举目四望,满地都是薄薄的卵石和青绿的低草。这环境和他先前在原野上一路行车时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他朝遥远的前方看,果然瞧见天河岛幽深宛转的山谷。
即使是在梦里,轻羽也忘不了自己手头的工作,于是他向着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谷前进。在梦里,飞行不会累,可他扑扇翅膀飞了很久很久,直到梦里红灿灿暖融融的太阳落到山谷背后,他都没有飞到目的地。梦中的天空和原野和现实没有多大的差别,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黑暗犹如决堤的河水,毫不留情地蔓延。
轻羽不禁有些慌,他不喜欢夜晚,没有云之民喜欢夜晚,在过于黯淡的环境里,他们那习惯了太阳光的眼睛几乎什么东西都看不见。在这里等着太阳沉湖可不行,他紧张地四下张望,希望能找到点足够自己躲藏的庇护所。就在这时候,轻羽看到了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轻羽甚至不愿意将其描述为生物,那就是一个个手脚细长到极致的人影在地面上阴暗地爬行。它们的躯干也长得离谱,目测从头顶到脚底能有四米,可肢体却还不如轻羽这个壮年男性粗。夕阳的光芒将它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扭曲的瓜藤、像田里的木支架、像云岛飘到寒带时枯黄的草叶,这些东西构成了它们的身体,再以诡异的幅度和姿态,佝偻着身子、四脚并用地行走。
轻羽从来没有见过这种东西,他见过的动物就没有长这样的……不,也许是见过,他陡然想起那白日里拼出的骸骨,复原出来应当就是这模样。他吓坏了,可在梦里他发不出声音,他周围的空气就像凝固了,不管怎么扇动翅膀他也无法移动分毫。更糟的是那些东西发现了他,他能看到它们纷纷抬起头,露出一张张很像人但更瘦更长的脸,然后它们展开同样窄长的翅膀,腾空而起,直冲冲地对着轻羽飞来。它们的手纷纷伸展开,那也是很像人,但细长得多的手……
“啊!”
这下轻羽可算是叫出声了,他从床上“腾”地坐起,惊出一身虚汗。身体脱离了噩梦,可意识还没有完全清醒,他像受惊的小兽梗着脖子扭头四处看,确定了刚才那还是一场可怕的梦境,才慢悠悠地重新躺下。真丢人,一个大男人居然被噩梦吓醒,他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打滚,感觉一定是营地的床太硬压着翅膀睡不习惯的问题。
宿舍的窗户面向东方的山涧,有淡淡的白线在远天显露,那是太阳即将升起的昭告。看到这皓白的天光,他不由感到犹如得救般的轻松。好太阳,我就眯一会儿,把噩梦的不适感驱散就起来上班,他这么想着,缩在翅膀窝里继续沉沉睡去。
这一次,轻羽没有再梦到怪东西,待他安眠一觉彻底清醒后,却发现红太阳早升得老高了。完蛋,这回不仅做了噩梦,还迟到了!轻羽立即骂骂咧咧地起身洗漱,赶往挖掘场,这时候,那太阳早爬到了山谷的半腰,睡懒觉的匍匐者都已到场,正站在仓库外面一边对技术员们的挖掘工作指手画脚、一边对着姗姗来迟的轻羽似笑非笑。轻羽撇嘴,径自走进室内,见鸣泉正站在地图前做标记贴照片。
“有了大发现,睡得那么好啊。”鸣泉打趣道。轻羽只好尴尬地笑笑,去检查他的“大发现”——昨天还好端端躺在地上的类人骸骨,现在却被盖上了一张大白布,像裹死人似的,从头到脚遮得严严实实。
“这是什么意思?”轻羽茫然。
“啊这,大伙要求的。”鸣泉赶紧帮忙将白布移开,“大家说这东西看着怪可怕的,干脆把它遮上。”
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觉得这鬼东西造型邪门啊,轻羽听后不禁还有点宽慰。他正想就自己夜里的噩梦发表些感想,站门口的熙泽就扭头搭了个腔:“好奇怪哦,你们做考古的还会怕人骨吗?”
他这一句揶揄,倒引得见惯了云之民枯骨的鸣泉也认真了起来,回答道:“说实话,我看人骨反倒不怕,但这个东西,感觉有点发怵。大概是因为长得像个畸形病人吧。”
此话说到轻羽心坎里了,他想起他的噩梦、和在梦中诡异爬行的人影,接话道:“如果你看到个长得很像原人,但比例上和原人有些微妙差别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
熙泽歪头想了一会儿,笃定地摇头:“不会,真不会。我有几个土人朋友,我觉得他们毛茸茸的挺可爱。还有最近很流行的那个林人明星,呵,林人的大脚板穿上高跟鞋,那身材,简直就是妖孽!”他一边说还一边斜着眼睛痴笑,惹得轻羽忍不住也斜眼看他,就像在看个变态。
但噩梦造成的阴霾并没有随着聊天打趣消失,即使吃过午饭后那太阳升得老高、几乎以垂直的角度炙烤着山谷的低洼处,轻羽走在食堂往工地的路上时依然能感受到一阵一阵的阴风在山谷底部卷。这样的心境下就连午休刷手机都没什么乐趣,轻羽便决定离开谷地,去太阳能够充分晒到的山坡上走走。
轻羽正如他的族姓那样,张开翅膀像片轻盈的羽毛,飘上附近的岩壁。他手脚和翅膀并用连飞带攀跃过陡峭的悬崖,来到较为平坦的坡地。站在山上,视野可比山谷里强太多了,艳阳母神平等地照耀着地面上的一切,照在他的身上和脚边的浮土,还有远处山谷之外望不见边的平原。轻羽极目远眺,还能看见平原之上他前些天出发时的那个镇子,就是蜿蜒天河畔的一颗黑点。
轻羽迈腿在山坡上漫步,觉得自己的心情变好了许多。他喜欢这样辽远宏大的风景,能让人感到自身渺小的同时却不至于气馁,他为能融入这样伟大的风光之中而感到欣喜。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古生物学,那些从未有人真实目睹过的生物,它们曾经存在的时间和空间都远远超越了现代人的想象。有关生命的故事延续了数十亿年,作为古生物学家他穷极一生也只能看到其中的零星点点。但这并不让人丧气,他知道作为生命一员的自己也能参与这场有关演化的宏大叙事,终有一日他的物种也能在生命的宏图上留下属于自己的印记。
他有一茬没一茬地放飞思维,没注意看四周的环境,直到身边响起一声“咔嘎”的尖啸声,他才回过神来。一只快赶上半个云之民高度的青鸟正站在悬崖的边缘,低着头支起耳羽、翘着尾巴竖高长翎,不安地嘎嘎叫唤。这是云洲最常见的掠食动物,脚下抓着吃了一半的白毛球鸟,嘴上还沾着血渍,显然被打扰了进食。
轻羽被鸟叫声和扑腾羽毛的摩擦声吓了一跳,还以为这在野外随便走走遇上了什么危险的兽鹫,定睛一看是个青鸟,可算缓过劲来。他蹲下身、收敛翅膀,让大只的人身看起来和青鸟差不多高度,再摊开双手示意自己没有恶意。那青鸟歪着头看了他一会儿,便收起耳羽、放下尾巴,扑腾两下翅膀,继续自顾自地吃毛球。
还好是个青鸟,青鸟不会找云之民的麻烦,云之民也不会伤害青鸟,这是两个物种在文明的历史中共生成千上万年养成的默契。想想直到现在,农户依然会雇佣青鸟帮忙照看农场、驱杀入侵的鸟群和飞兽,云之民也会帮助青鸟寻找和保卫繁殖场、还在城里留出适宜青鸟歇脚的绿林广场,轻羽就感到欣慰。他刚才说什么来着,演化史不会忘记,这就是云之民的存在留下的足迹。
可能也是因为共生历史的关系吧,看匍匐者吃肉会让轻羽感到恶心,但青鸟大啖血淋淋的生肉却不会。他还特地靠近了些,饶有兴致地观察这青羽大鸟美餐的场面,不得不承认有时候看看活生生的动物比研究死气沉沉的骸骨好玩。他看那青鸟以大脚掌按住圆滚滚的猎物,然后用凿子似的尖喙用力敲击球鸟庞大的头骨,在坚韧的骨头上凿出一个个坑洞。
“咔咔咔”,青鸟碎骨的声音就像是某种启示,轻羽愈发觉得这凿子似的伤痕好像在哪里见过,越想越熟悉。他一拍脑门,在青鸟讶异但不警惕的目光中展开双翅跃下了高崖。
轻羽一路飞腾着回到仓库,一进门就听见匍匐者正在和鸣泉、和几个好奇原人科研的学生们吹牛,侃侃而谈原人和亲缘种土人之间的故事。他说原人最早是从土人里分化出来的,被“兄长”暴揍一顿后离开山林来到平原,才在广袤天地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在那之后,他们原人和土人不计前嫌共同发展,一个盘踞深山、一个称霸平原,最终原人发展出了被称为“文明”的伟业,土人和其他猿猴们也得以分一杯羹,成为了原人的附庸。
熙泽把这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唬得前来围观的学生们连连喝彩。但轻羽现在没精力听故事,他扒拉开聚在仓库门口的人群,冲进室内,一把掀起盖在怪人骸骨拼图上的幕布。他在学生们惊异的叫声中捧起怪人的头骨仔细查看,在那白净干燥的枯骨上,果然有他刚才看到的那种,像凿子敲出的裂纹。
“鸣泉,这事你应该比我更清楚……”轻羽心里有个想法,但他需要先求证,“云之民和青鸟的关系具体是什么样的?我是说,从古文明的角度。”
鸣泉还沉浸在熙泽讲述的原人故事里呢,尽管不知道对方为什么会提这个问题,他还是像个导师那样耐心做出解答:“是这样的,我们在距今十二万年前的遗迹里就发现过兽骨上同时有羽神和青鸟的咬痕,距今六万年前的陶器上也描绘过先民和青鸟共同狩猎的景象,甚至一起抵御神鹫和巨龙的攻击。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羽神和青鸟之间曾经因为那些巨型掠食者的威胁而团结在一起,并且存在长达数万甚至数十万年的合作共生关系。由于这些渊源,青鸟和我们还有很相近的文化结构,他们也信仰太阳和雷霆,挺有趣的。”
“你是说,有很长一段时间,羽神和青鸟都是合作狩猎、需要对付相同的威胁、并且文化包括祭祀行为也应该差不多,是吧?”
鸣泉点头:“你可以这么理解。为什么问这个?祭祀坑里并没有青鸟,实际上我见过人祭,但还没听说过有用青鸟献祭的。”
“因为这里不是祭祀坑,也不是单纯的墓地,我们不会吃掉献给神的祭品。”轻羽说这话时,还特地看了一眼匍匐者,而后者已结束吹牛,好奇地凝视着他,“这里是战场。”他说,抬起手,向仓库内的每一个人展示骇人的怪人头骨,和骸骨之上清晰无比的、青鸟在攻击和啃食时才会凿出来的痕迹。
听到这话,熙泽激动地吹了声口哨,他接过头骨认真看了一圈,接话道:“有意思,这就说得通了。原人也有类似的战场遗迹,胜利者会把战友的尸体整齐放好,而敌人就随意扔在四周……甚至,”他想了想,才继续说,“甚至,如果双方有什么深仇大恨的话,胜者会把败者的尸体全部剁碎用来泄愤,就跟这个坑的情况一样。不过这种遗迹总的来说很少,野兽那边反而要多一些,像狼就会把敌人吃掉,然后将碎骨撒在牺牲的战士旁边。”
尽管很想吐槽这个匍匐者又在一本正经地说些野蛮的话,但看到这些骇人的怪骨头和坑中诡异的骸骨排布,轻羽说不出口。被区别对待的骨头堆、让人害怕的异种造型、曾和青鸟一起战斗的痕迹,这些加在一起令他不得不承认,这匍匐者给出的解释很可能是事实。
“但是我不明白,按理来说这些怪人是你们的亲缘种,和你们的关系就跟土人和我们一样,为什么会有深仇大恨?要我说,你们应该是和这种东西共同抵抗巨龙,而不是和大鸟,相似的生理结构比较容易相互理解和合作才对啊。”匍匐者还在说话,他托着腮帮子喃喃道。
鸣泉背靠着墙,看着原人毫无负担地把玩手中的头骨,又看向原本盖在怪人骸骨上的白布:“可能是因为,我们会觉得相似的结构很可怕吧。”
“有道理。”熙泽将头骨还给轻羽,无奈叹息,“可惜哦,本来你们也可以有附庸亲缘种的。”
啧,我们的附庸兽神属亲缘种是全身长毛的,比裸皮的可爱多了。轻羽心里暗自嘀咕,他看到鸣泉也耸了耸肩,深感那是只有匍匐者才能够理解的叹息。
挖掘工作还在继续,在新发现的引导下,研究员们不再按照祭祀的方式挖掘,而是铺开更大的范围。几天以来,挖掘场地再度扩展了足足两倍,一些弓箭、长矛、兽骨号角、诸如此类能够证明战争存在的痕迹也在墓地远处的山谷低洼地带被发现。看来这里确实如轻羽所想,是一个来自远古的战场。
由于大部分疑问都得到了解答,挖掘工作稳步推进,熙泽的顾问工作已告一段落,收拾收拾准备离开了。他走的那天,轻羽和鸣泉都专程为他送行,驾飞车将他送去天河镇,再在那里送他转乘长途飞车去往最近的云岛都市。在云洲,只有大都市里才有和地面世界联通的机场,想到又得面临一两天的舟车劳累,熙泽就缩在座位里一边哀嚎一边晕车,看得轻羽忍不住又愉悦了起来——能帮上忙的匍匐者,依然还是弱小的匍匐者嘛。
三人在天河镇上最好的餐厅里吃了最后一顿散伙饭,出于对营地糟糕伙食的报复,熙泽点了很多肉菜,从禽鸟到飞兽,据说连平均一个月才能打到一头的兽鹫都给端了出来。这顿饭看起来就很贵,轻羽斜眼看负责带队主持这次野外工作的鸣泉,感觉对方的心都在滴血。
“好吃,果然好吃,真有甜味!”而匍匐者自然是不在乎肉是否昂贵,他大口大口地往嘴里送食物,吃得可开心了,“你们知道的吧,云洲动物甜食吃得多,肉也很甜的,可惜就只有来出差的时候才能吃得到。”甜不甜轻羽不知道,但看这匍匐者像个野兽一样胡吃海喝,确实远不如看青鸟觅食那样赏心悦目。正吃着,熙泽却突然停下了,低下头面露苦色,久久不发一语。
“咋了,吃肉还不开心啊?”轻羽调侃道。
熙泽指着自己的脸,说话声囫囵不清:“咬到……舌头了……”
“哈,动作那么夸张,咬舌头很痛吗?”轻羽笑道。
“出血了哎,你说痛不痛。”熙泽倒也不矜持,立即张大嘴伸出舌头来给轻羽看他被咬破的伤口。红彤彤血淋淋的舌头可一点也不好看,轻羽嫌弃地撇过头。虽然只是一瞬间,他敏锐的眼睛不仅看到了原人的舌头和血,他还瞥到了对方的牙,和云之民很相似、但又有些差异的牙:上下颌各有两颗比其他牙齿长得多的尖锐獠牙,和野外那些无肉不欢的野兽果然是一模一样。
轻羽不自觉地伸舌头舔了舔自己的牙齿,没有特化到能咬伤自己的尖牙,相比起来要平整多了,这是以植物为主食的牙齿。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件事,一件有关怪人骸骨的、非常重要的事。
他赶紧拿出手机调出自己拍摄的骸骨,还好他有把样本都拍照记录的习惯。他看到那怪人头骨的牙齿,和云之民一样,是平整的、以植物为主食的牙齿,而且那臼齿发达得俨然比云之民更加喜欢吃瓜果和蔬菜。
“我知道了。”他先是喃喃自语,接着激动地喊了起来,“我知道了!我们会选择青鸟而不是怪人是因为什么!”注意到这是在公共场合,自己似乎有些失态,他立即收声。
嘴停可是脑子不能停,好好想想,他确实是知道了,他想到一个可能性,一个有关和怪人的战争、有关恐怖感的来源的可能性。还有青鸟,他想到青鸟是吃肉的,他们如同武器的尖喙和大爪子就是为了吃肉而生的。他想到熙泽讲述的原人和土人分别占据平原和山川、最终称兄道弟的故事。他想起自己的噩梦,那些很像云之民但又不是云之民的怪物,想象它们和自己的先民有着相似的喜好、相似的食谱、相似的栖息地和相似的生活习惯。
可他们不能如此相似,云岛比地面小,适合生活的土地也少多了、小多了,小到无法承载太多生态位一致的生灵,于是这些东西必然和云之民经历过漫长到无法想象的生存竞争,只有云之民活了下来。所以他们云之民才会和食性、栖地都有所差异的青鸟结成联盟,所以他们才不愿直视那些怪人的骸骨。毕竟凡有接触、必留痕迹,演化史是不会忘记的,那场决定生与死的战争在云之民的基因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些像人却不是人的东西,最终成为了幸存者延续数万年也未醒来的梦魇。
轻羽一股脑给同伴们讲出了自己的推测,个中精彩之处听得鸣泉忍不住鼓掌。这个古文明学家也深谙物种、环境与文化演替的关联,他沉思片刻,鼓励地说道:“这是你发现的物种,轻羽教授,给它取个名字吧。”
“恐怖……”轻羽想都没想脱口而出种名,可应该接在后面的属名他却怎么也说不出口,“鸟。就叫‘恐怖鸟’吧。”
“呵,我还以为你要叫它‘匍匐者’呢!”熙泽笑了。
可轻羽笑不出来,他看着眼前这个豁达的原人,看着他和云之民趋同演化出来的样貌、看着他和云之民同为文明物种的举手投足,他想到自己那没来由的蔑视和远离,一脸愕然。
灵感源于很早以前某天看到的一个有关恐怖谷效应的假想,说也许恐怖谷效应的起源并非单纯对机器人、尸体、病人、畸形或者别的什么对人自身的恐惧,而是来源于最早的最早,当人科人属还有很多物种的时候,尼安德特人的恐怖竞争在智人的基因里留下的痕迹
原人有不少亲缘种依然健在,那么就让总是搞种族歧视还不自知的鸟人来扮演这个角色吧(X)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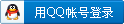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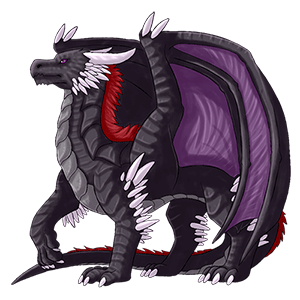
 发表于 2022-11-9 22:46
|
发表于 2022-11-9 22:46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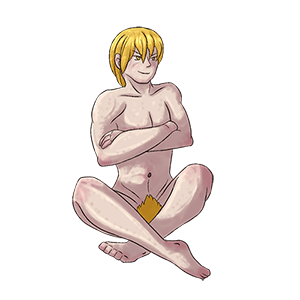
 发表于 2022-11-24 19:22
|
发表于 2022-11-24 19:22
| 









 (饞
(饞

